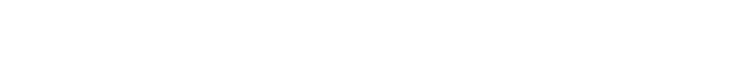俞益期《交州笺》:槟榔“性不耐霜”
作者 张作奇
俞益期《交州笺》,即《与韩康伯笺》,是指晋代俞益期写给好友韩康伯的一封书信。 据郦道元《水经注》卷三六载:“豫章俞益期,性气刚直,不下曲俗,容身无所,远适在南。”吴九龄修《(乾隆)梧州府志》:“俞益期,豫章人,寓交州,著《交州笺》。”清代文献学家、藏书家严可均《全晋文》卷一三三载:“喻希。希字益期,豫章人,升平末为治书侍御史,累迁至将作大匠,有集一卷。与韩豫章笺。案韩康伯为豫章太守。”可见,俞益期即喻希,益期乃其字,他曾历任治书侍御史、将作大匠等官职,著有《喻希集》一卷传世。

俞益期,正史无传。谢旻《(雍正)江西通志》卷六六载:“俞益期,豫章人,性气刚直,不下曲俗,远适交州,与豫章守韩康伯书论槟榔以寄况,著《交州笺》传于世。(豫章书)”《钦定古今图书集成》之《晋文学名家列传》收录《俞益期传》曰:
益期,豫章人。性气刚直,不下曲俗,容身无所,远适交州,与豫章太守韩康伯书曰:惟槟榔树最南,游之奇观,子既非常,木亦特异,余在交州时度之大者,三围高者,九丈余……但性不耐霜,不得北植,必当遐立海南,辽然万里不遇长者之目,自令人恨深。著《交州笺》传于世。
据上可知,《交州笺》是俞益期寓居交州时,写与同好韩康伯的一封“寄况”信函。而此时,韩康伯在俞益期家乡豫章任太守。韩康伯,房玄龄纂《晋书》有传,云:
韩伯,字康伯,颍川长社人也。清和有思理,留心文艺。举秀才,徵佐著作郎,并不就。简文帝居藩,引为谈客,自司徒左西属转抚军掾、中书郎、散骑常侍、豫章太守,入为侍中。……转丹阳尹、吏部尚书、领军将军。
《交州笺》并不仅仅是一封普通书信,而是一种对晋时交州实况的记录。讲述了在交州的见闻,原文已佚。但由于内容新奇,被南北朝许多著作引用。又因诸书征引各取所需,而将其割裂成条。据掌握的资料显示,此文主要记录了一个人物并予以颂扬,描绘了一种植物并表达其情感。
首先,记录了一个人物——伏波将军马援。俞益期通过《交州笺》向韩康伯讲诉他在交州的所闻所见,而“见闻”最多的是马援故事。文章对马援建设交州的事迹、交州的社会习俗、稻米农作和蚕桑养殖以及槟榔、椰子、香木等物产进行了详细介绍。如:
马伏波昔开道,篙迹凿石犹存。
马文渊昔立两铜柱于林邑岸,此有遣兵十馀家不反,居宁寿灵岸南,南对铜柱,悉姓为马,自为婚姻,有三百户。交州以流寓,号曰马流。言语饮食,尚与华夏同。山川移易,铜柱今没在海中,正赖此民,以识故处。
“马伏波开道”,“此道废久”,“铜柱”,均与马援相关。对铜柱数量准确记载为两根,还说“铜柱今复在海中,正赖此民,以识故处也”,寻其意铜柱已没于海中不可见。而铜柱附近的居民,“自称汉子孙”,是马援留下的遗兵“马流”,这些遗兵的姓氏、婚姻、户数无不历历在目。
马援(公元前14年—公元49年),字文渊,扶风郡茂陵县(今陕西省兴平市)人,西汉末年至东汉初年将领,东汉开国功臣。据《后汉书》之《马援列传》载:
玺书拜援伏波将军,以扶乐侯刘隆为副,督楼船将军段志等南击交阯。……明年正月,斩徵侧、徵贰,传首洛阳。
援所过辄为郡县治城郭,穿渠灌溉,以利其民。条奏越律与汉律驳者十馀事,与越人申明旧制以约束之,自后骆越奉行马将军故事。
二十年秋,振旅还京师,军吏经瘴疫死者十四五。赐援兵车一乘,朝见位次九卿。
伏波将军即东汉马援。东汉建武十七年(公元41年),马援奉光武帝刘秀诏令率军南征,曾屯兵湘潭昭山下的昭滩,埋锅造饭,卸鞍饮马。因此,昭山又名马山,有纪念、叨光马援的意思。据清·王闿运《昭山》有:“上有昭滩,名因马援。山潭之号,更在其前。”又据清康熙《湘潭县志》载:
马山在县东三十里,截江而起,耸立万仞,仰抱湘流,森秀如画,盖邑之华表山也。

据此,我们可以想像:马伏波很有可能把槟榔和嚼槟榔的习俗带到了湘潭。其基本逻辑是:马援出征南越,途经并驻军湘潭昭山(马山);平叛交阯后穿渠灌溉、发展生产,种植水稻、槟榔,以利其民;汉军瘴疫死者十之四五,嚼食槟榔以御瘴疠;班师回朝再经马山,将嚼食槟榔习俗带到湘潭。这虽然没有文字佐证,但完全有这种可能性。

其次,描绘了一种植物——槟榔“性不耐霜”。俞益期写给好友韩康伯的信中,介绍晋时岭南交州一带的历史、地理、风俗、物产等内容。特别将“槟榔”,为信南游之可观。俞益期《交州笺》即《与韩康伯笺》云:
槟榔,信南游之可观:子既非常,木亦特奇,大者三围,高者九丈。叶聚树端,房构叶下,华秀房中,子结房外。其擢穗似黍,其缀实似谷。其皮似桐而厚,其节似竹而穊。其内空,其外劲,其屈如覆虹,其申如缒绳。本不大,末不小;上不倾,下不斜:调直亭亭,千百若一。步其林则寥朗,庇其荫则萧条,信可以长吟,可以远想矣。性不耐霜,不得北植,必当遐树海南;辽然万里,弗遇长者之目,自令人恨深。
“槟榔,信南游之可观”:信者,坚定其辞也;南者,标方所也;游者,标功夫也,物不能迁,则人远游也;可观,标效用也。既备述槟榔之奇特非常,又不得不以嗟叹收束之也。此树非南游不可观也,而其奇特非常又不可不观也,以是有恨,而难绝也。
《交州笺》中“槟榔”内容详实、叙述生动,类同于“风土记”和“异物志”等作品。如杨慎《升庵集》卷五三“文章物状”条在征引其“槟榔”条后便感叹说:“此分明画槟榔图也。”这是对《交州笺》记述完整、内容真实的一种肯定。李昉撰《太平御览》卷九七一《果部》亦云:“槟榔树,大围丈余,高十余丈。皮似青桐,节如桂竹。下本不大,上末不小。调直亭亭,千万若一。森秀无柯,端顶有叶。”
槟榔“性不耐霜,不得北植”。槟榔树扎根岭外广袤之地区,不得北植,“北”指的是南岭之北,此见其局促也。这里也暗指汉武帝曾北植热带草木“无一生者”的事实。“弗遇长者之目,自令人恨深”。我能见而长者不得见,此树非南游不可观,而其奇特非常又不可不观也,以是有恨,而难绝也。益期以不合于流俗,远去交广,以故多识岭表方物,其果欲康伯亦南迁乎?盖康伯有忧于益期,益期乃多言方物,示方物可以忘忧,而去康伯之虑,此真良朋也。
(原载张作奇编著《槟榔百典》,待出版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