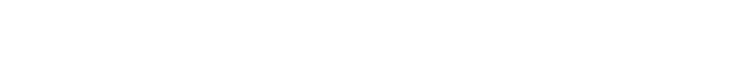中原槟榔从异树到中药食材的历史考查
在古代中国,具体何时何地何人开始嚼槟榔,实无详细的史料记载。中国最早记载槟榔的文献是西汉司马相如的《上林赋》,文中有“留落胥邪,仁频并闾”一组词。其中“仁频”一词应来自爪哇语“jambi”的音译,即“槟榔”之意。
司马相如是如何得知“仁频”便是当今的槟榔?缘于汉武帝遣伏波将军路博德和楼船将军杨仆率军南征,并于公元前111年结束了南越国的统治,班师带回了大量在南越国才有的热带植物,其中包括槟榔,并移植在扶荔宫。
荔枝也是在列的南越特产,汉末魏初的《三辅黄图》一书中载“汉武帝元鼎六年,破南越,建扶荔宫。……自交趾移植百株于庭,无一生者,连年移植不息。后数岁,偶一株稍茂,终无华实。”
槟榔与荔枝一样,对生长的温度和湿度要求较高。既然荔枝很难在北方开花结果,想必槟榔也是如此,更勿奢望品尝这异域奇珍的滋味。因此,笔者推测当时的中原并未有人嚼食过槟榔,西汉时期(公元前202年~公元8年),槟榔在中原地区通常只是以“南越异树”的形象出现。
东汉时,议郎杨孚(南海郡番禺人,今广州市海珠区)所著《异物志》中首次记录了岭南嚼食槟榔的习俗。虽《异物志》原书散佚,但北魏贾思勰著《齐民要术·卷十·槟榔》引载的《异物志》文字中有槟榔的描述:“......剖其上皮,煮其肤,熟而贯之,硬如干枣。以扶留、古贲并食,下气及宿食、白虫,消谷。饮啖设为口实。”意思是:将槟榔剖开并煮熟,再将扶留藤和牡蛎灰与其搭配食用,不仅味道更加甘美,还有“下气及宿食,消谷”的作用。或许正因为槟榔具有下胃气、降宿食的效用,所以槟榔在东汉时期(公元25年~220年)才逐渐演化成了一种药材。
东汉末年,华佗首次将槟榔纳入药方。
其方一:“上痞者,头眩目昏,面赤心悸,肢节痛,前后不仁,多痰,短气,惧火,喜寒。又,状若中风之类者,是也。宜用后方:桑白皮(阔一寸、长一尺)、槟榔(一枚)、木通(一尺,去皮。一本作一两)、大黄(三分,湿纸煨)、黄芩(一分)、泽泻(二两)。”(《华氏中藏经·卷中·辨上痞候并方》)
其方二:“中痞者,肠满,四肢倦,行立艰难,食已呕吐,冒昧,减食或渴者,是也。宜用后方:大黄(一两,湿纸十重包裹,煨,令香熟,切作片子)、槟榔(一枚)、木香(一分)。”(《华氏中藏经·卷中·辨中痞候并方》)
中医术语里的“痞”,是指病人自觉胸中或胃脘部胀满不适,有似辣非辣,似热非热,似饥非饥,闷涩不适的感觉。这两个药方里都含有槟榔这味药,说明槟榔具备提神醒脑、下气、消食、祛痰的功能,与杨孚所记录的槟榔之用不谋而合。此后,槟榔作为一味中药,在历史长河中逐渐获得了“四大南药之首”的地位。
从西汉的“南越异树”到东汉的中药,槟榔的身份完成了一次转变,其中原因仍须琢磨。前文提到,中原人第一次接触到的槟榔是来自南越,直到东汉时才发现了其药用价值。这说明药用槟榔有可能是西汉汉武帝攻打南越国时,由南越人传予中原人,直到东汉时才被广泛接纳;也有可能是东汉时官民被发配至岭南,通过当地人或自身摸索得知槟榔有抵御瘴气的功能。“瘴”首见于《后汉书·列传·刘虞公孙瓒陶谦列传》描述公孙瓒的长官坐法徙于日南(今越南广治省东河市)的场景:“太守当徙日南,瓒具豚酒于北芒上,祭辞先人,酹觞祝曰:‘昔为人子,今为人臣,当诣日南。日南多瘴气,恐或不还,便当长辞坟茔。’慷慨悲泣,再拜而去,观者莫不叹息。既行,于道得赦。”可见对医学技术还很落后的古代人来说,岭南的瘴气实乃恐怖之极。及至唐代,槟榔首次被称为“洗瘴丹”。《岭表录异》中提到“交州地温,不食此(槟榔)无以祛其瘴疠。”这意味着在东汉时,槟榔仍只是作为一味普通中药,其祛瘴的作用也许只有居住在岭南一带的人才知晓。直到唐代,槟榔“洗瘴丹”的名号才打响开来。
(许璐供稿)